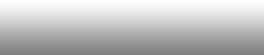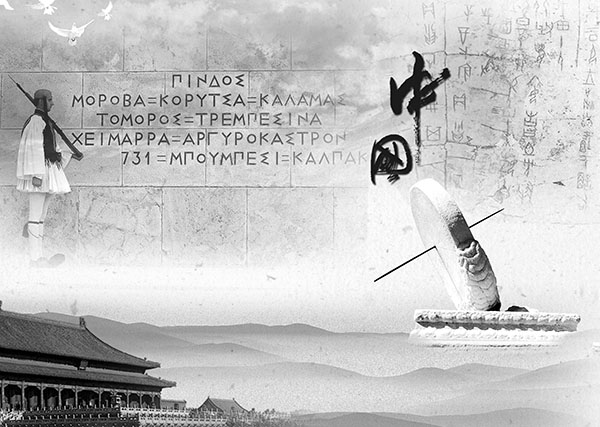
希腊语-中国话
It’s Greek to me! It’s Chinese to me! (这对我如同“希腊语”一样天书繁难!这对我如同“中国话”一样神秘难懂!)当“通天塔”的语言被变乱之后,这两句关于神秘事物和繁难语言的俗语,勾勒出了人类语言的两极,一端是中国,一端是希腊。
中文和希腊语之间,横亘着冰雪覆盖的青藏高原,一座喜玛拉雅山。自然的阻隔,也是语言的屏障,青藏高原以西,是印欧语系(Indo-European)的地盘,以东,是汉藏语系(Sino-Tibetan)的地盘。这屏障曾在公元前320年前后阻挡了来自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脚步,他和他的军队徘徊在这样一座冰雪严寒构成的天然屏障面前,像一组浩浩荡荡的动词催动的名词,期待着冰雪严寒的翻译和通行。

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考证寻查,在中国和印度的边界,至今仍然生活着亚历山大大帝军队的后裔,他们的语言中保留着古希腊的词汇,连他们自己也不甚明白的奇异祭拜习俗中,可以在古希腊的古典多神教祭祀礼仪中得到溯源。
这些据称是古希腊人亚历山大大帝的后裔,是一篇古老文本的残篇断简,这些来自西方文明故乡的肉身文字,一代代延续着古老的血缘生命,执拗地等待皑皑冰雪的翻译,期待莽莽高原的通道。
在今天,每一个从中国来到希腊的人们,都应该在现代航空器飞越青藏高原之时,朝机舱云层下看一眼那些没有名字的种族,我们在机舱里轻松舒适的自东向西的飞行,使得两千三百年前的那次东征,那次文本翻译的请求活动,显得如此悲怆。在历史的时间表中,捷足的阿基琉斯在跑,缓慢的乌龟也在移动。
It’s Greek to me! It’s Chinese to me! 这两句话早在两千三百年前就在喜玛拉雅山下的高原上相遇,希腊——中国,孤独的星球上两个村子的村民敲击着横亘千里的冰雪墙壁,似乎相互都听到了呼喊,知道隔壁有人声,只是听不清。
是到了这两个村子的人们见面的时候了。
苏格拉底-孔子
苏格拉底每天清晨就早早起床,从今天雅典“安齐罗齐彼”(Ampelokipoi)地铁站附近的家中漫步走向卫城脚下的“古市场”(Agora),在那里他和人们交谈,有时候也辩论,话语不多,要言不繁,人们听到了他的话,常常摸不着头脑,对那些看似清楚明白的话语却不甚明了,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数日甚至经年之后,那句话才在内心轰隆一声炸响。

苏格拉底和孔子一样,身边有一些年轻人围绕,说过不少的话,却自己几乎不写一个字,苏格拉底和孔子身边的年轻人留意着老师的每日谈话,用简陋原始的方式把这些散发着日常身体余温的话记录下来。希腊和中国,《柏拉图对话录》和《论语》,东西方哲学的肇源伊始文本,都是这一问一答的对话文字。哲学的基本概念“辩证法”(Dialectic,Διαλεκτική),就来源于希腊语的对话Dialogue。你来我往的语言,一问一答的对话,竟然构成了东西方哲学的共同源头,亲爱的西边的小村子希腊,亲爱的东边的大村子中国,你们好!
孔子和苏格拉底都在哲学的滥觞之始关注到了人与人的关系,他们首先关注的是人的问题,他们俩不约而同地关注着善、爱、幸福、美德等——这些最为基本的词汇仍然在今天是每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最为迫切的日常关键词。
雅典的好天气是在夏天,夏天的好时候是在清晨日升时分和黄昏的日落之后,早晨的风从雅典的群山吹向爱琴海,黄昏的风从温暖的爱琴海送回到比大海更快清凉下来的群山,古代雅典人的早起习惯是这吹来吹去的风建议和催促的。
苏格拉底早早起床,正走向人们谈话辩论、买卖生意的古市场。善,爱,幸福,美德……等关键词正在苏格拉底宽阔的胸膛里蒸腾酝酿,一会儿,卫城周围橄榄树林里的年轻人就要和苏格拉底开始谈话辩论了。这是苏格拉底的最后一日,这是柏拉图《斐多篇》记载的重要一日,判他死罪的毒芹已经在准备调制了,他今天要对身边的一两个年轻人谈谈心中那个在关键时刻出来说话的“小神”的声音,这是作为人类的任何一员,都会在内心存在的一种声音,是每个人心中天然存有的道德律令的声音。“君子慎独”,在寂寥无人的地方,在你的内心深处,那个声音,那双眼睛,一直在看着,守望着。
两千年时长的人类的一天才刚刚开始,在山东鲁国的杏树林中,一个年轻的弟子开始向孔子询问,希望找到可以一言以蔽之的一个终极问题:“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样一个“恕”字,将在三四百年后被基督耶稣一次次提及,在新的世界格局面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平衡尺度,将会被后世的德国人康德以另一种文本翻译的方式描述,这样的一句话被镌刻在康德的墓碑之上: “有两种事物,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希腊作家卡赞扎基斯曾经两次游历中国,他在《中国纪行》中写到:“孔子和苏格拉底只是两个面具,面具下面是同一副人类逻辑的面孔。”
苏格拉底走向古市场的早晨,才刚刚开始;鲁国杏林的问题,才刚刚提出;亲爱的两千年一朝夕的这一天——你好!
东方的大轴-西方的大轴
公元前500年前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奇迹时代,中国有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列子;在印度有《奥义书》和佛陀;在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印度和希腊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在同一个时间达到了各自的智慧高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把这一时期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

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会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这是一根横贯东方西方的大轴,这根大轴曾经推动过世界,正在推动世界,将继续推动世界。
今天,希腊人和中国人常常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唐人街、希腊城相遇,成为患难与共的朋友。这两个古老文明的后裔流散在世界各地,他们在背井离乡的创业伊始,都被迫着不约而同地操起锅铲瓢勺,用希腊餐饮和中国美食作为自己生存谋生的手段。当整个东西方世界都在享用着古代希腊和中国文明带来的精神营养之时,世界强迫着这些文明发源地的后裔们在喂饱世界自己的胃。
希腊和中国,是这古老文明大轴的东西两端。
每当世界需要整体性解决之道的时候,这些植根古老土地的文明,将会挺身而出,为世界提供新的参照和坐标。“9-11”纽约双子星大楼的轰然倒塌,是老子第九章“揣而锐之,不可长保”的直观写照,“和而不同”、“上善若水”,世界重新思考东方观念中何以能“天长地久”的智慧。当西方以“罗格斯”为中心的世界开始陷入重重困境之时,世界开始倾听来自中国柔和缓慢的风声。
柏拉图的学苑的门楣上镌刻的是:“不懂几何学者莫入。”孔夫子的教学理念建立于:“有教无类。”希腊橄榄树林的风声,鲁国杏林的花香。
苏格拉底注意到“德”在调整人与人等社会关系上的重要意义。他的“美德即知识”凸显了“德”的重要性。他对整体的人类抱有和老子、孔子一样的坚定的乐观态度。
马克思说:“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希腊和中国就是这个世界的数学,这两个文明古国以数学的精确,在记录着历史的脚步。对待希腊和中国的态度,是世界和历史本身是否成熟和自觉的一个标尺。这些曾经转动世界大轴的民族的后裔们,在轰鸣热闹的厨房里谦卑地用充满油渍的手拿起锅铲炒勺,为世界可耻的大胃在工作。当世界开始把这些厨房里劳作的希腊人中国人请出来,谦恭地向他们请教希腊语的“德”( ἀρετή -Arete)的发音和中文的“仁”字的写法和深义之时,世界清凉的早晨才开始醒来……
世界正在醒来,在雅典的橄榄树林,在鲁国开花的杏林。
上一篇: 中欧文明对话会在雅典举行
下一篇:经济文化双轮驱动中希关系发展
最新动态
NEWS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Add:Κepamikou 52 Athens Greece T.K.10436
Tel:00302105226074
E-mail:cgmce88@hotmail.com